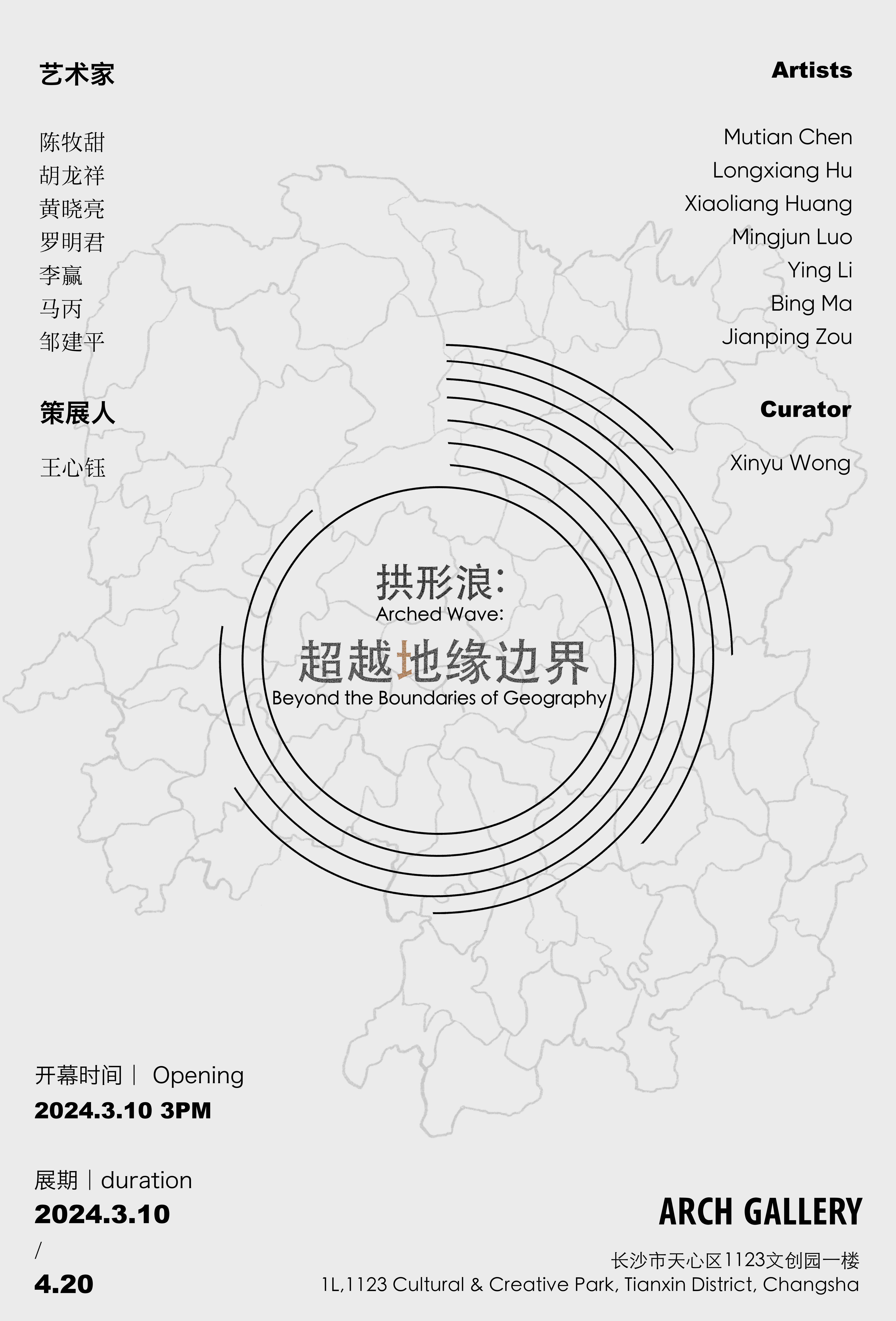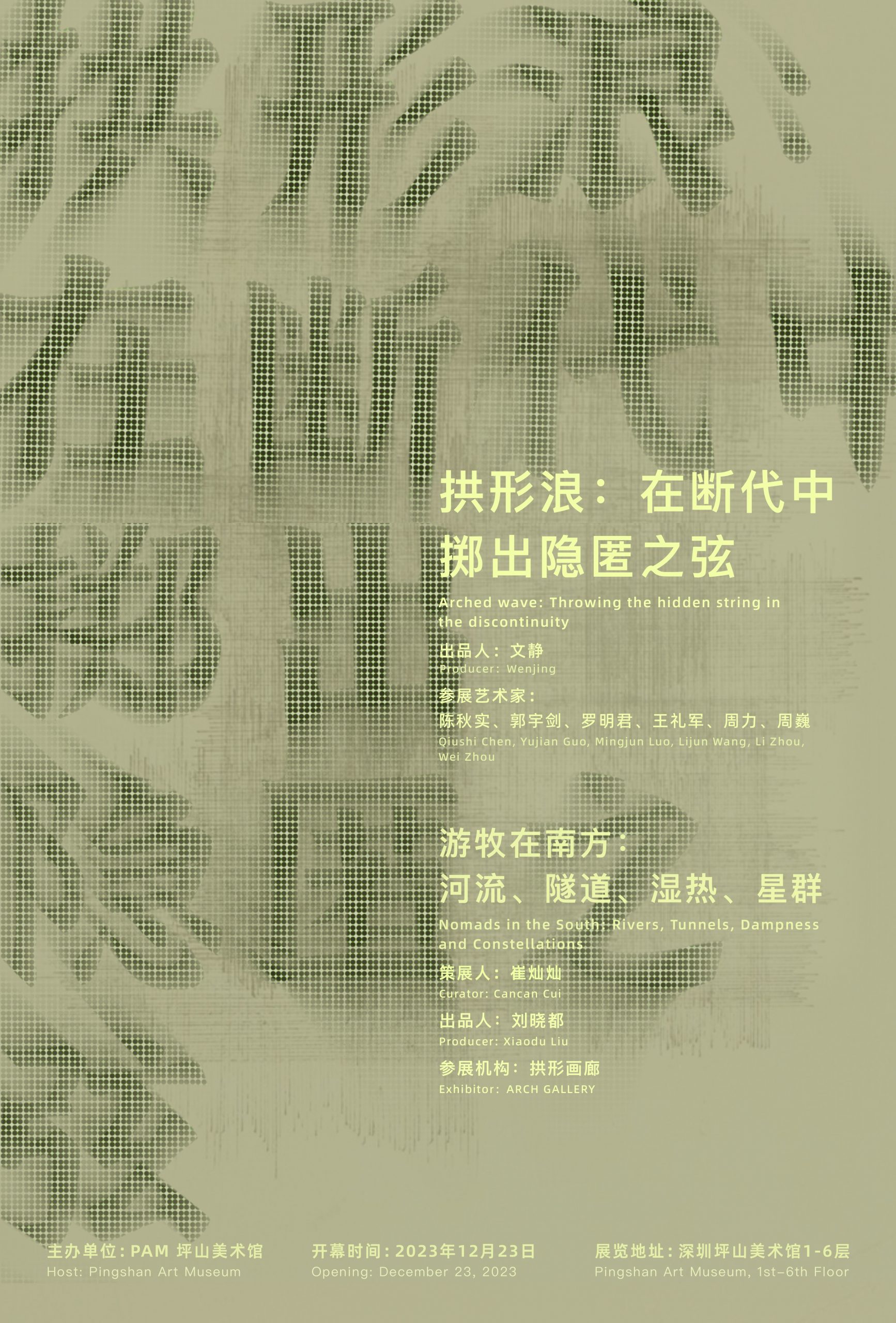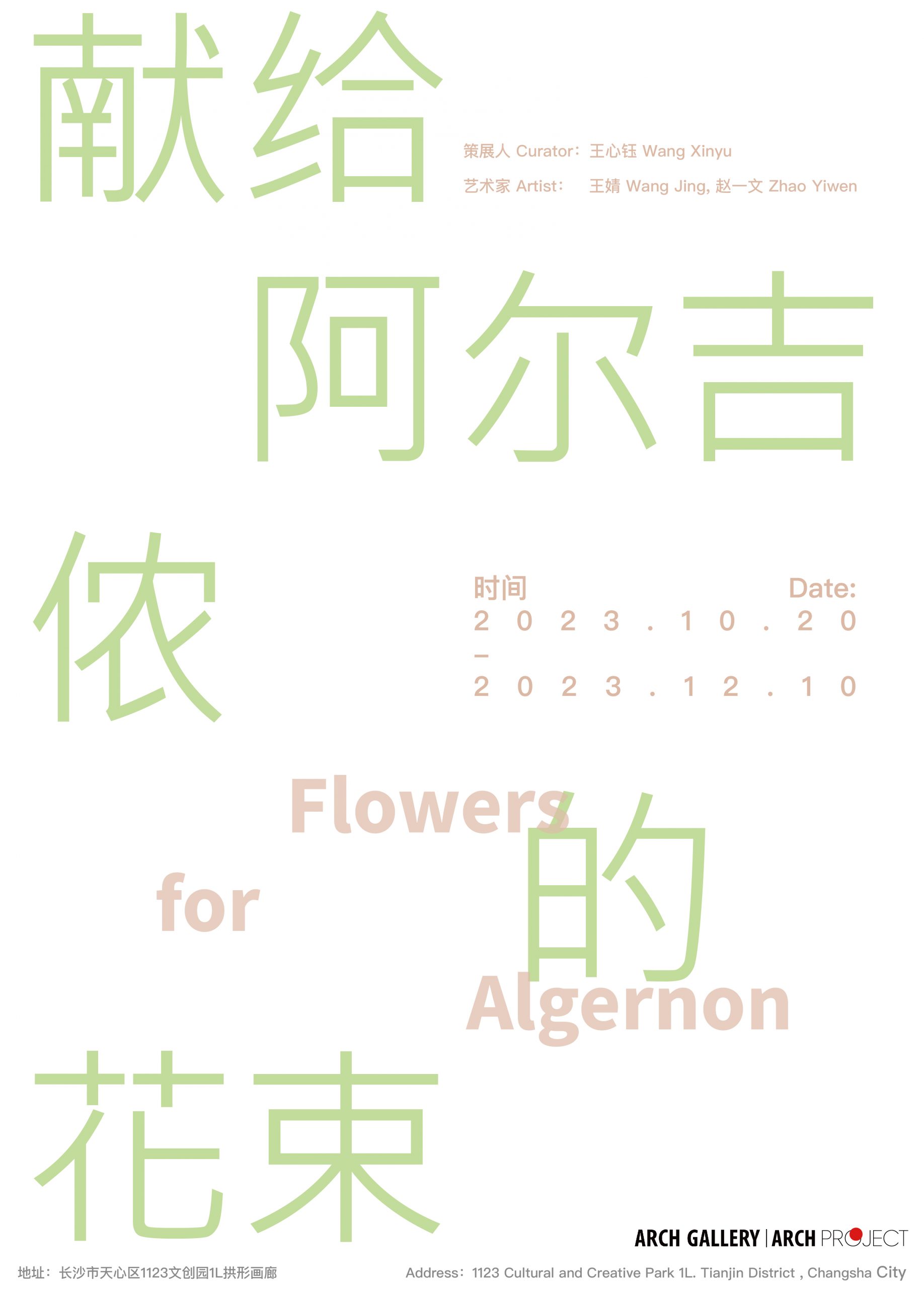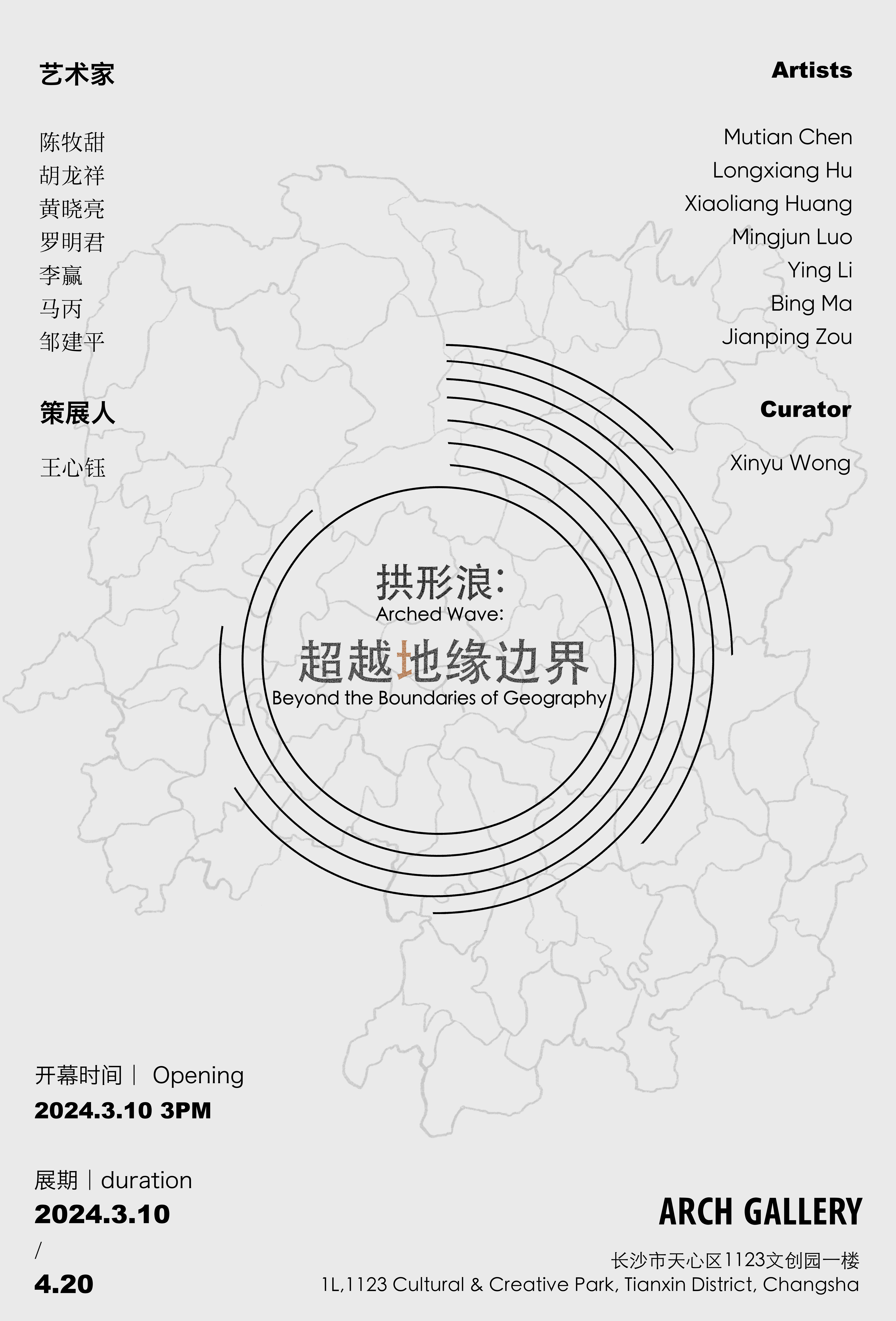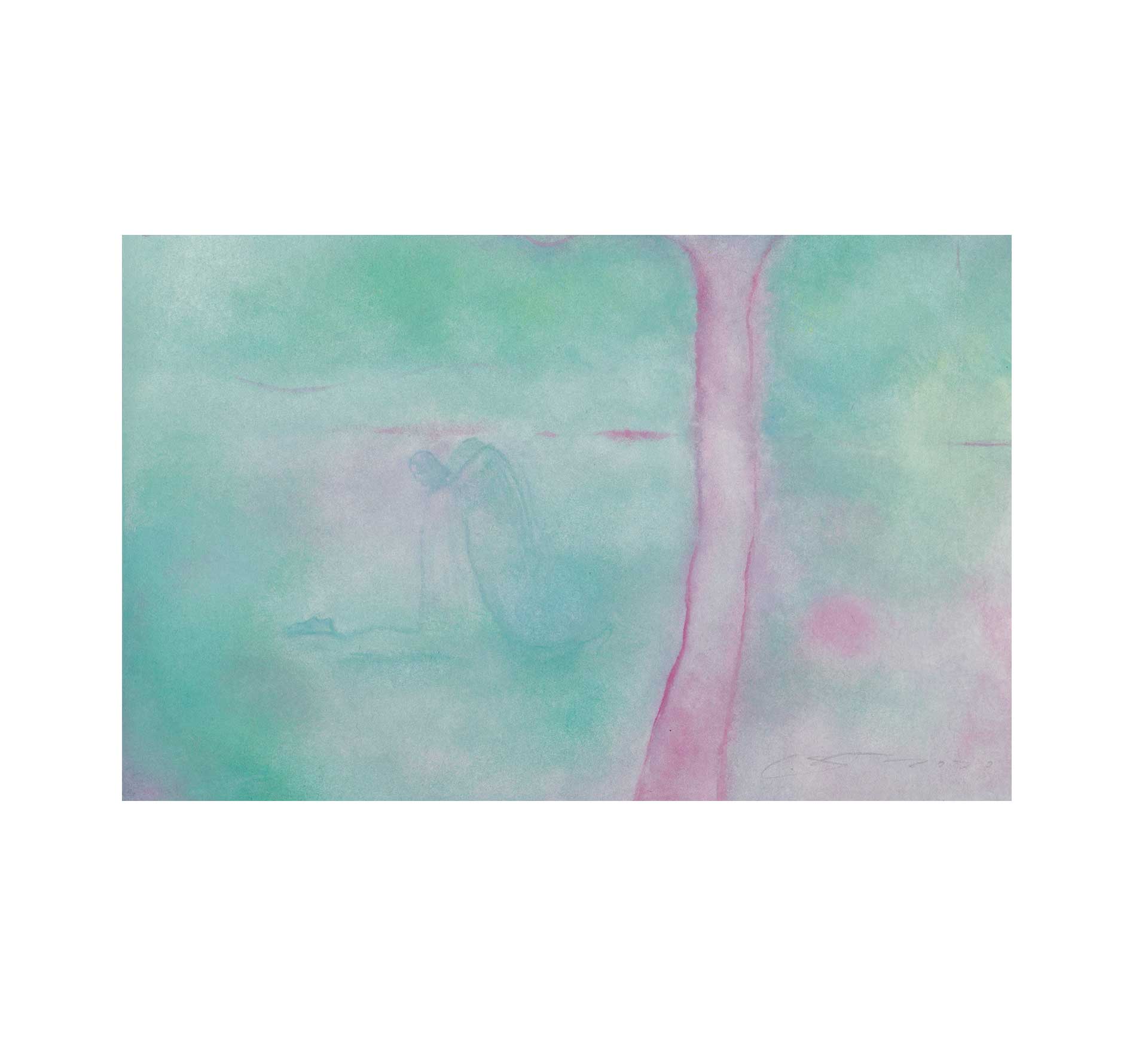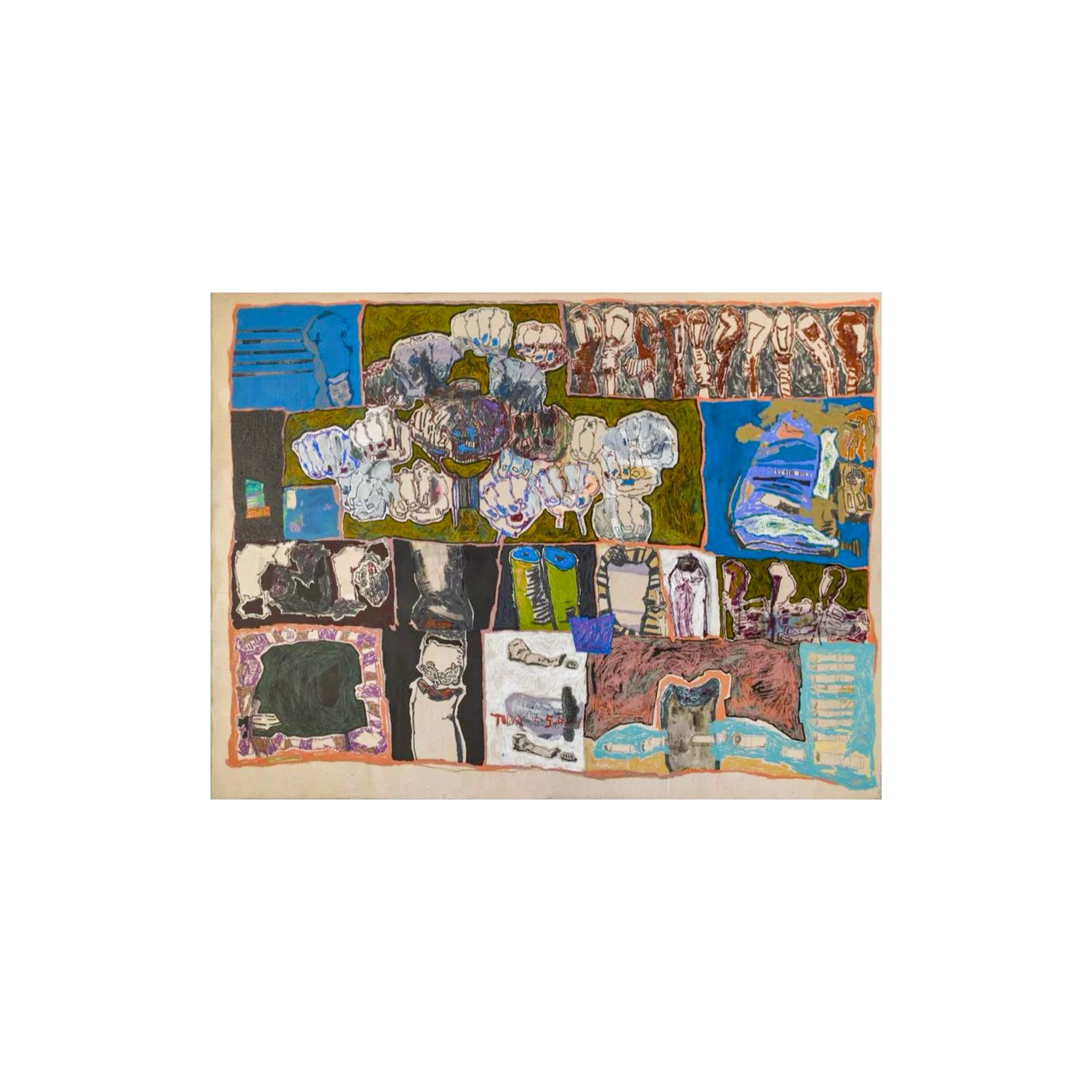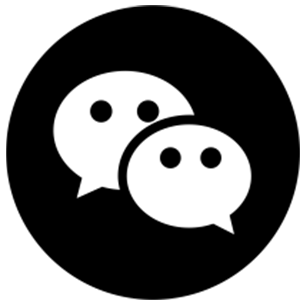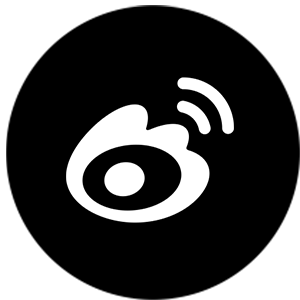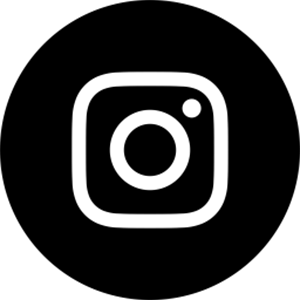眼前
艺术家:陈秋实、范诗磊
策展人:胡奕航
2022.04.09 – 05.17
ARCH PROJECT 于4月9日呈现实验项目「眼前」。ARCH PROJECT此番与艺术家陈秋实和范诗磊合作,展现他们近年来代表性的作品。
「眼前」直击意识形态的观看方式。在这种方式下,我们的“观看”不夹杂任何思考,或者说我们无需思考。一切都已被意识形态接管。不论是范诗磊的多媒介作品所营造的异托邦空间对文化工业的破坏性行动的反诘,还是陈秋实横跨多种摄影方式的图像创作在现实中被他所针对的问题反噬——“生产不再意味着拥有解释的权力”对冲着新意义的建立,都会让我们成为“为了不上当而迷途(上当)的人”(Les non-dupes who errent)。这两位艺术家游走在问题与答案的边缘,留下给我们的,便是ARCH PROJECT希望和观众一同重新思考的眼前的新现实。
艺术作品能将现实折叠,以政治化的方式影响观看者视网膜上的成像。普鲁斯特叙述艺术为创造世界特异的表象方式。在他那里,世界是成千上万个——“就像每天清晨有多少双眼睛睁开,有多少人的意识苏醒过来”(追忆似水年华 卷五:女囚和女逃亡者)。在普鲁斯特的巨作中,世界作为零散的记忆被一个又一个视角所观察并因此折叠,我们的经验被无数次地覆盖。如同将写满文字的纸张反复折页,每一次的折叠在强调一部分信息的同时,也让一部分信息模糊。世界表象也因此变化。
无论是面对艺术作品还是现实,我们看到的是否是事物的真实的模样?正所谓“眼见为实”对视觉器官的准确性的肯定,似乎我们对一样物品看得越清晰;对一件事情剖析得越清楚;对一个运动分解得更详细,我们就偏向于认为自己越接近事物的本质。然而这种观察方式的问题在于,它过于强调视网膜成像的价值,却忽视了那些深刻影响着我们的意识形态。这种方式将实体都当成工具。换句话说,当一双筷子只能成为一双筷子;一块墓碑只能成为一块墓碑;一张面具只能成为一张面具,如何去使用它们便是重中之重。而当我们对工具的功能越熟悉,我们对这些所谓的“工具”的认识就越少,我们的视野也因此变窄。
本质上的对世界的观看是对时间的感知。在面对穆斯林老人“为何留住时间”的质问时,安东尼奥尼“错愕无言”。在老人的眼中,停滞在拍立得照片中的影像,等同于死掉的过去。这个过去是一秒前的,一天前的还是一年前的,这都无所谓,唯一有所谓的是它失去了生命。若跟随穆斯林老人的角度思考,拒绝对过去的否定意味着对时间保持模糊的印象。过去、现在和未来总是在彼此之中。例如瓦尔兰是否领导过巴黎公社成为了记忆幻觉(déjà-vu),无产阶级的奋斗理想却在未来存在。当资本家为工人上下班的时间准确地设定到几时几分,工人的工作时间便成为了死掉的过去。昨日的工作和今日的工作毫无区别也无相关。至于明日的——还未发生的看上去也过于确定。用纳博科夫的话说:“未来只是另一种过时。”
被折叠过的纸张难以恢复原本的平整,但它们又恰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拒绝清晰的图像的机会。拿走纸张上方的重物,再单个铺开,无关方向的时间的运动——只要它不被“留住”——将让图像模糊。世界真实的模样,存在于磨损的折印中。
- 「眼前」展览现场。摄影:ARCH GALLE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