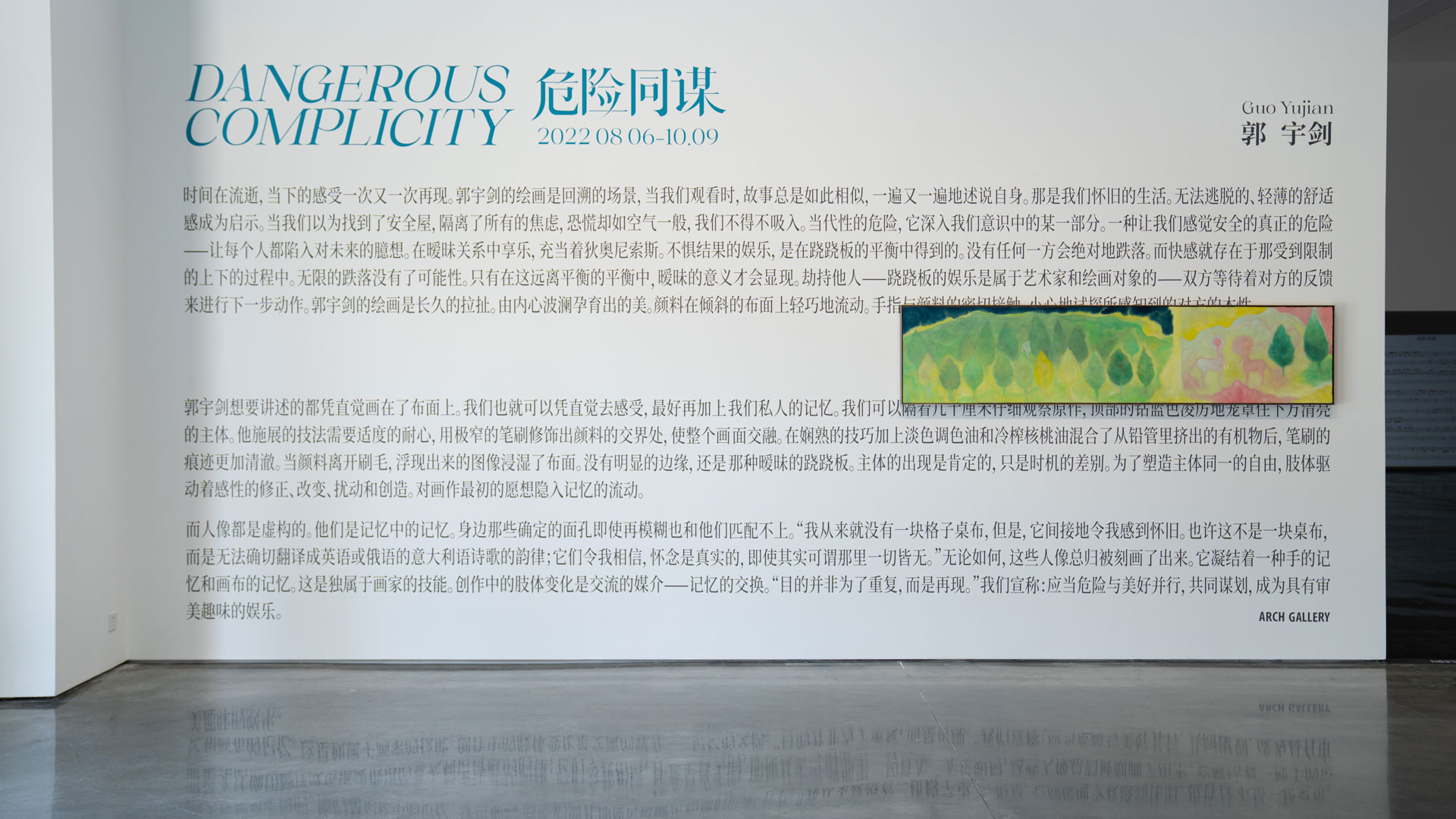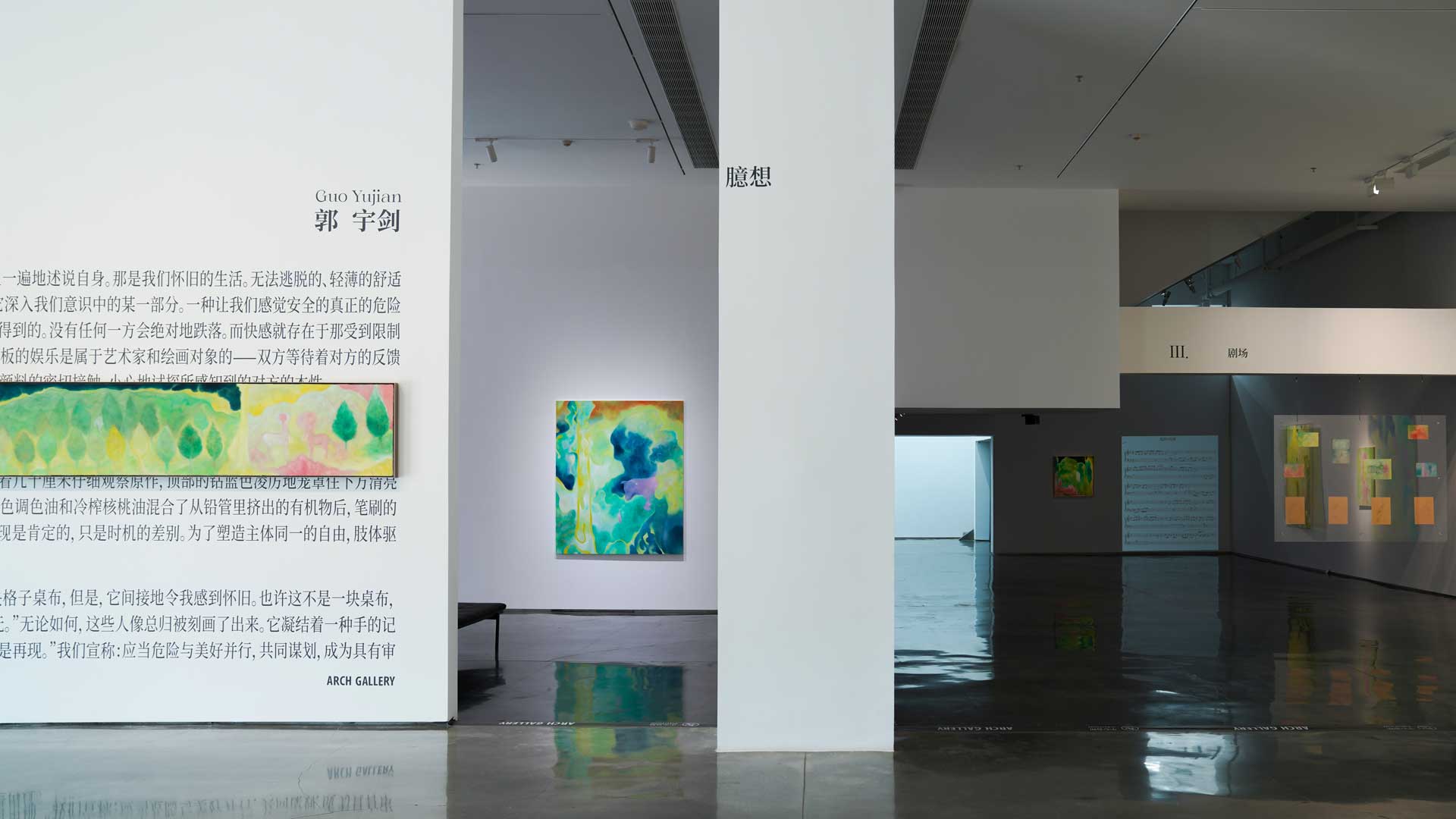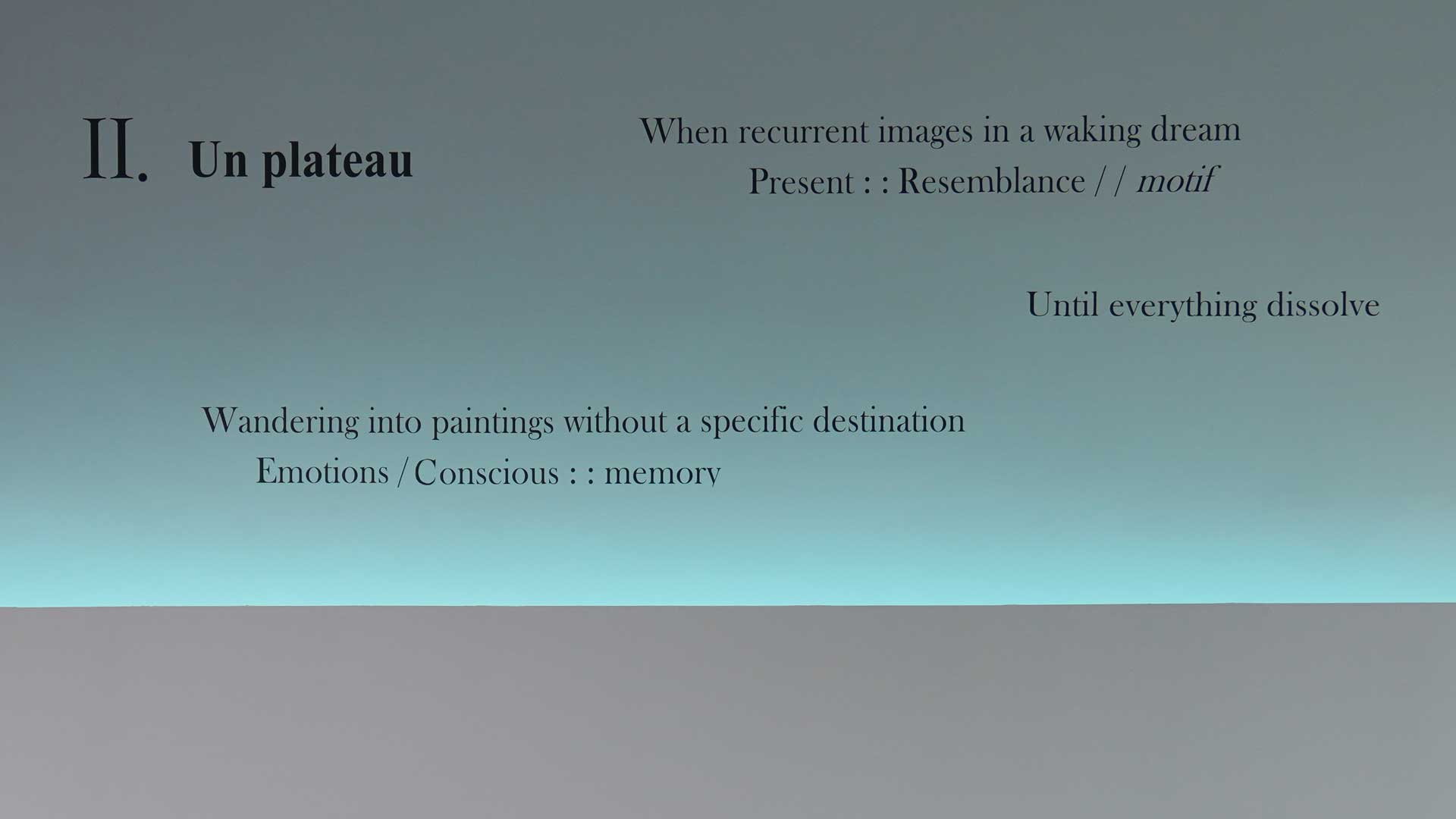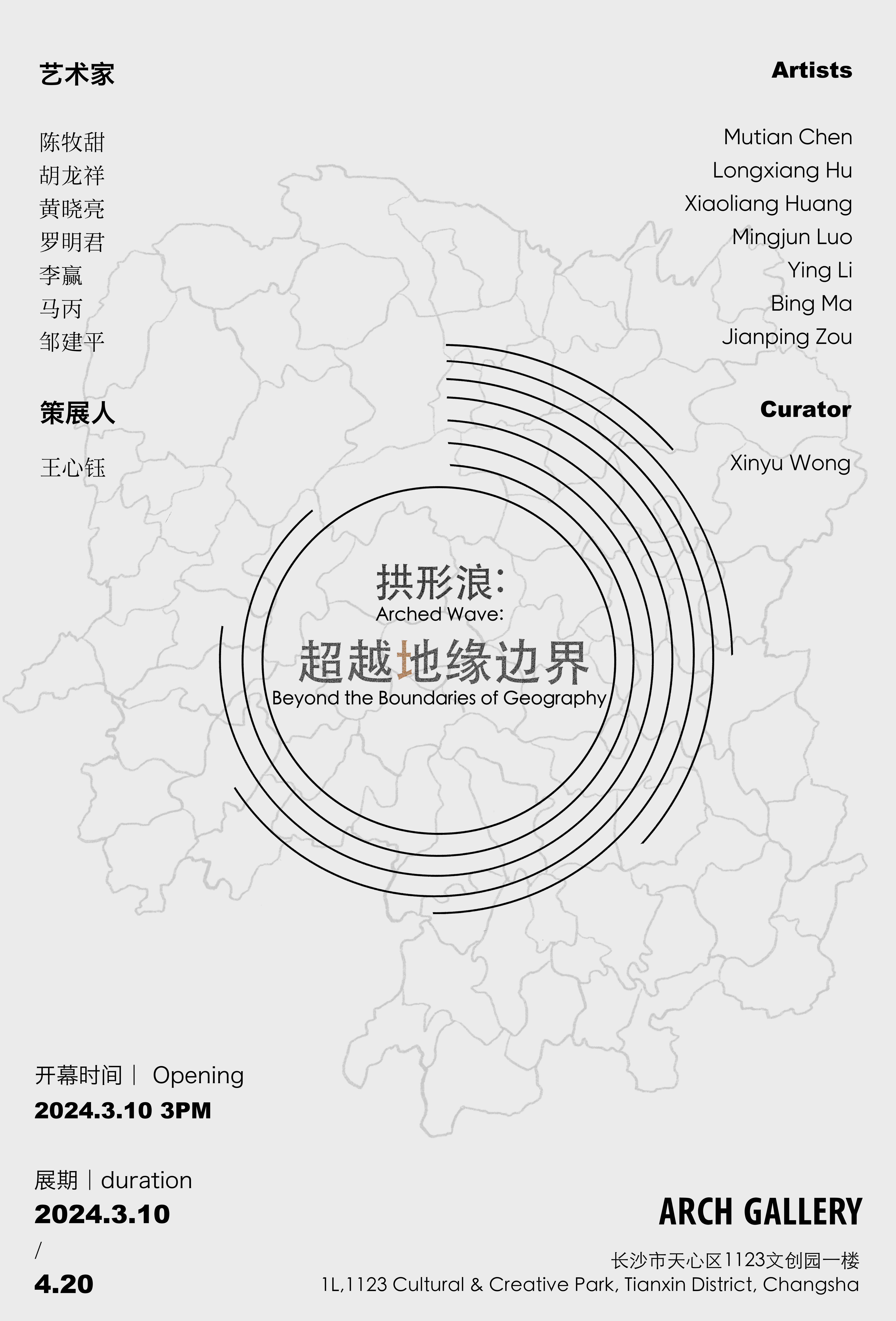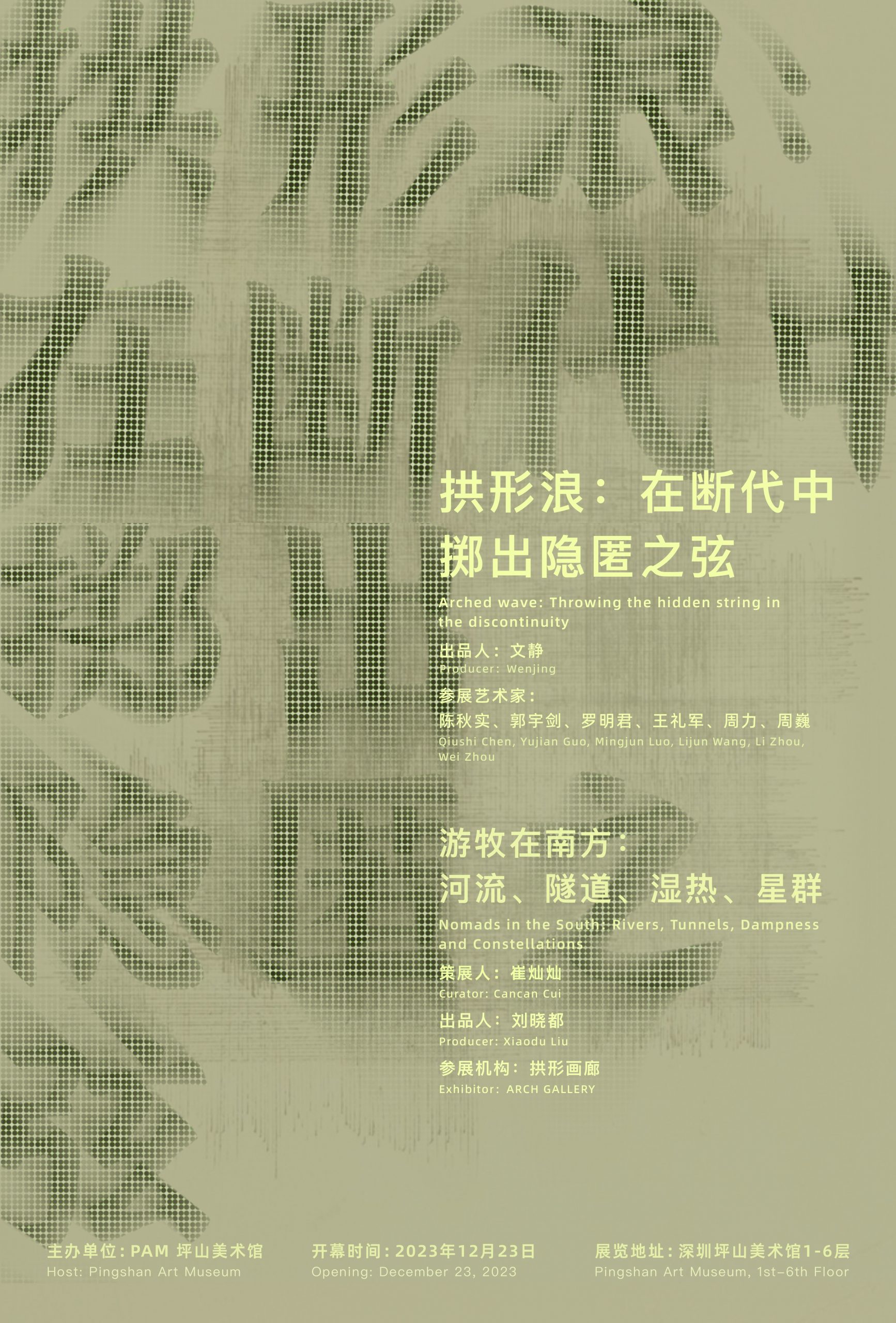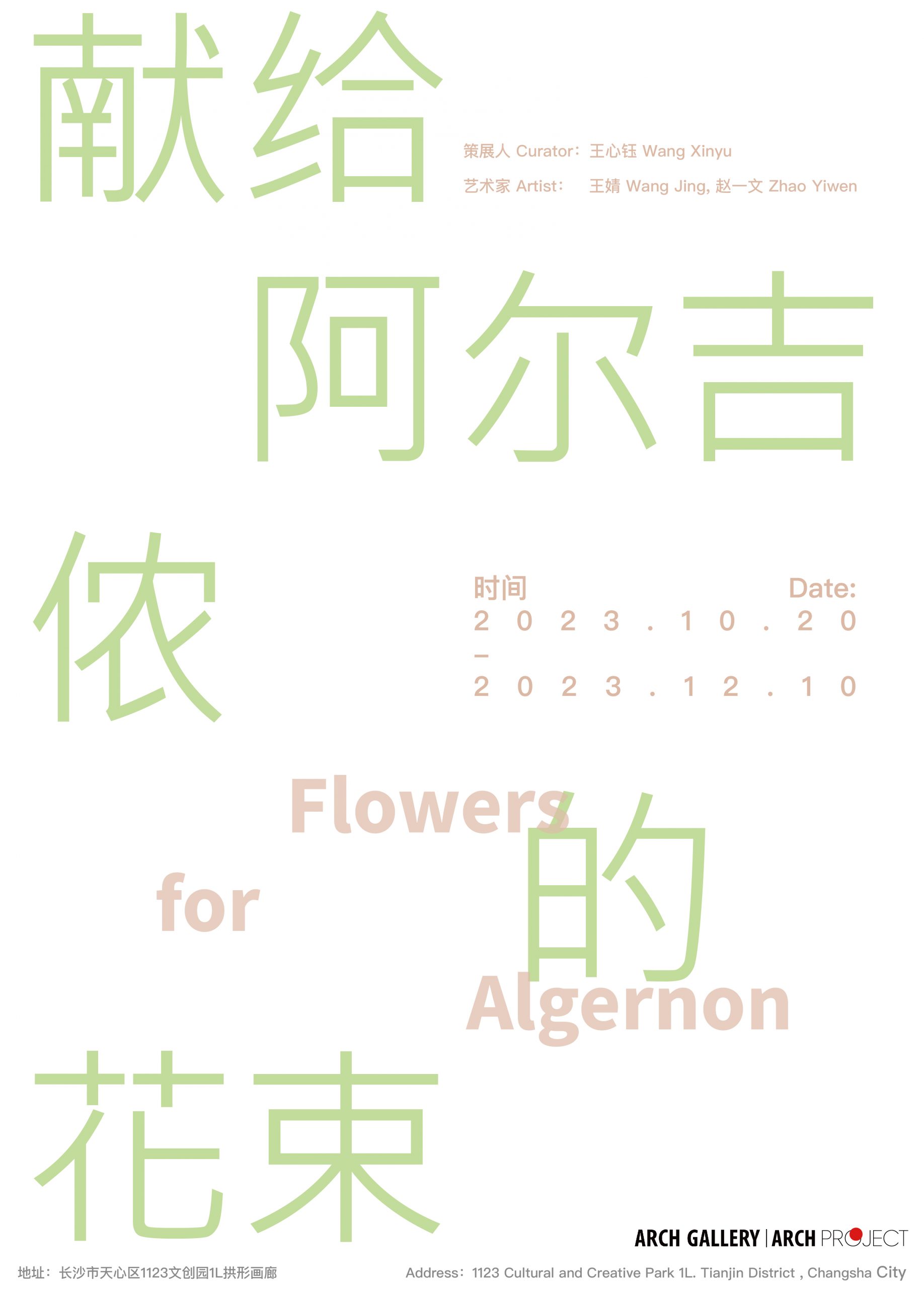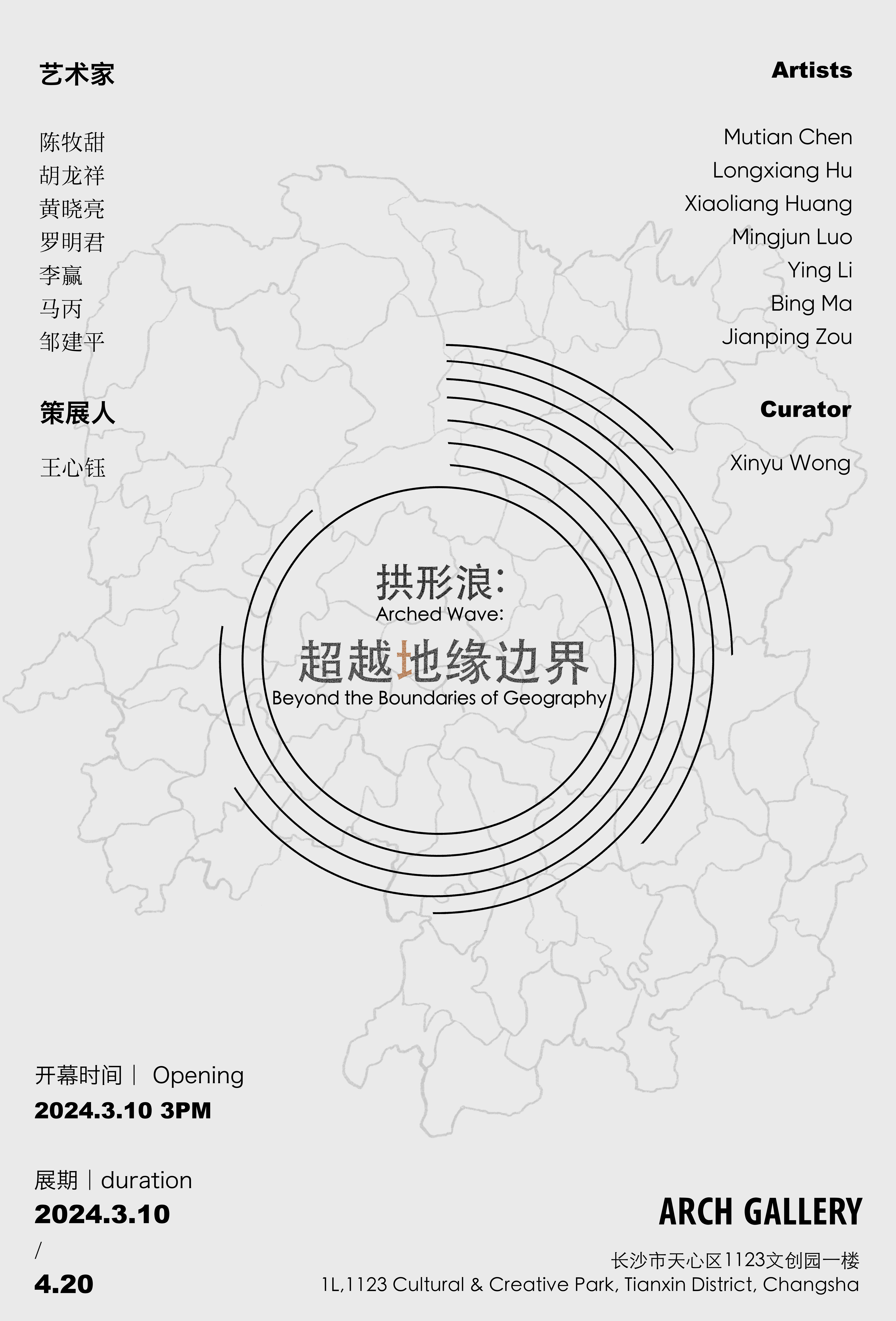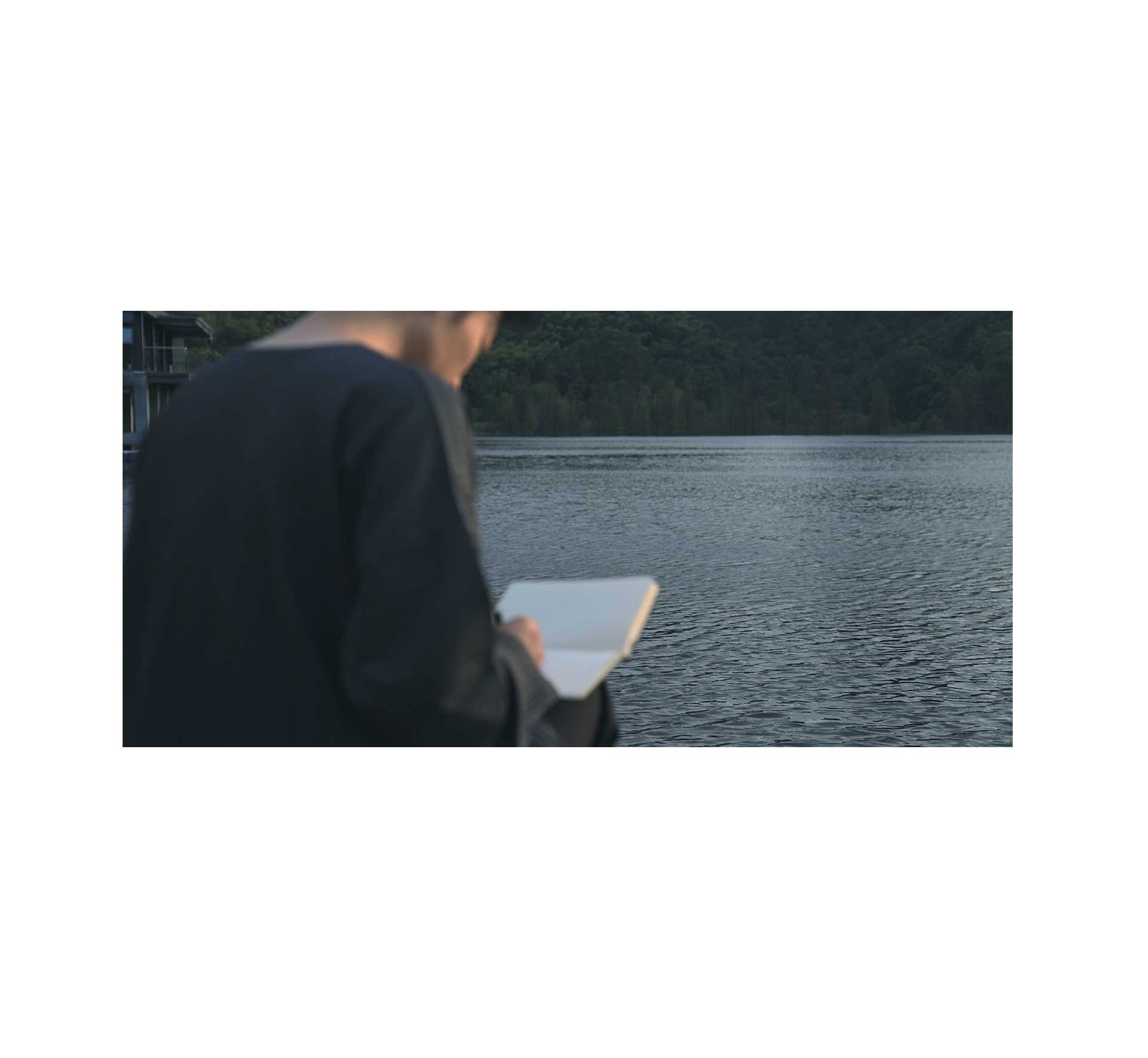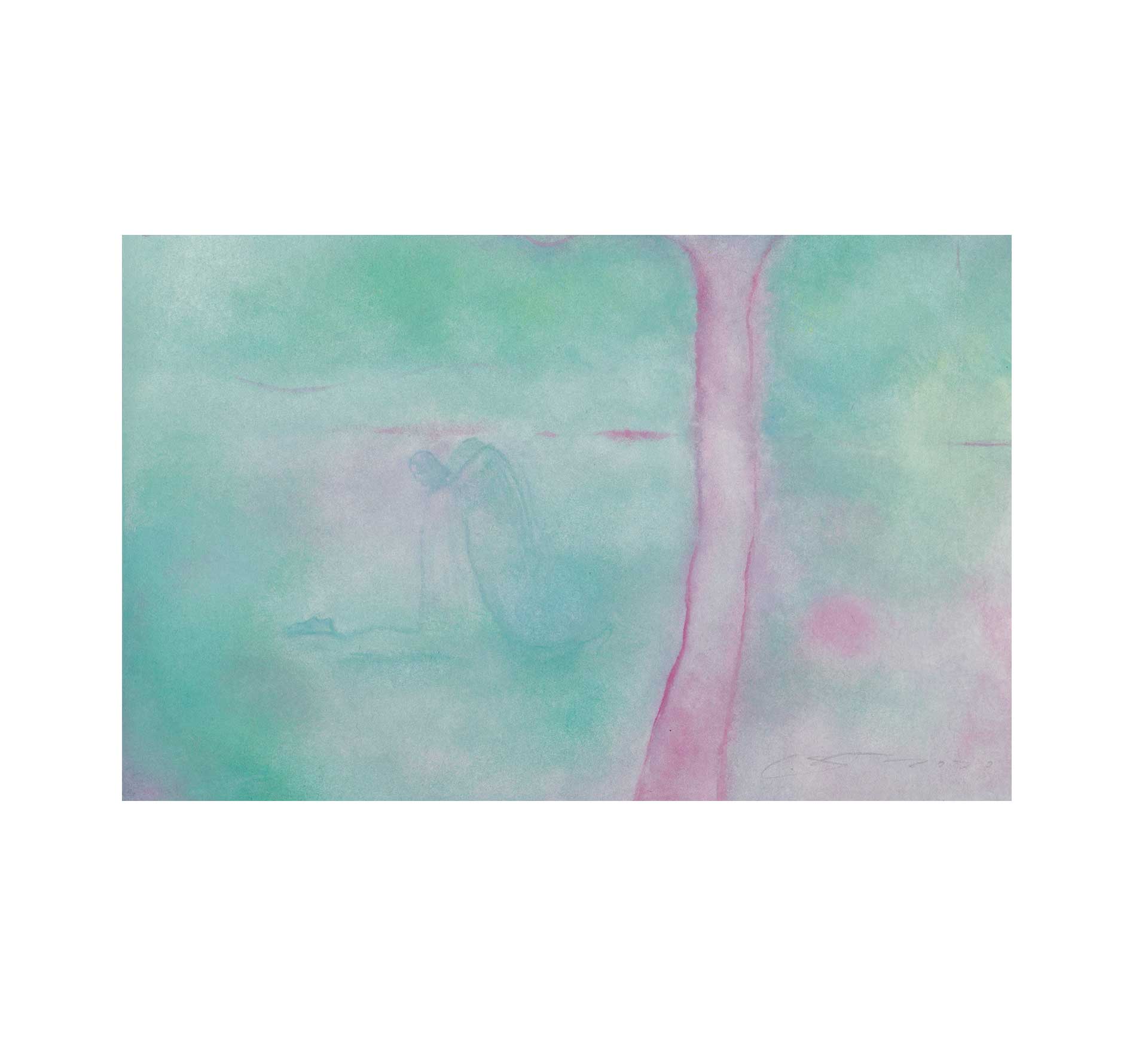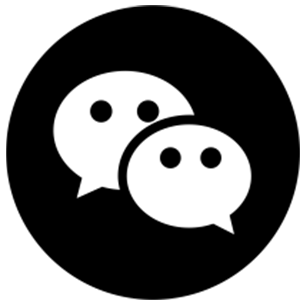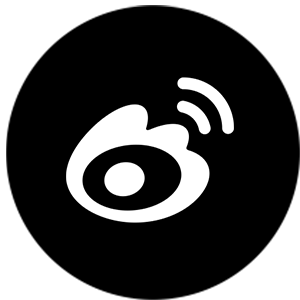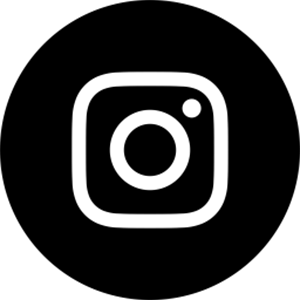ARCH REVIEW | 制造共犯
《制造共犯》
艺术家:郭宇剑
文字:刘广隶
- Dangerous Complicity, ©ARCH GALLERY 2022
- Dangerous Complicity, ©ARCH GALLERY 2022
这片平静的房顶上有白鸽荡漾,
它透过松林和坟丛,悸动而闪亮。
公正的“中午”在那里用火焰织成
大海,大海啊永远在重新开始!
当画作真切地逼近我们双眼,首先出现的是这首瓦雷里[1]1922年所写的《海滨墓园》[2]。机构策展人胡奕航、张汀芷与艺术家郭宇剑一起,将这次拱形画廊名为《危险同谋》的展览,用文字或符号分成了几大篇章:臆想、一座高原、剧场。许是有意为之,又或是无心之举,开篇选取的这段文字,饱含着诗人瓦雷里对家乡赛特港的深沉眷念。正如他与文学家纪德[3]通信中写的:“当心烦意乱的时候,当生活的波涛将我推回到想成为一个孩童的几何点上时,我的头脑中总会出现一个大海的影像,在那里,我耗尽了生命的最后一息。然后,我的存在与整个浩瀚的海洋世界融合了,我感到自己与之合二为一。”[4]瓦雷里去世后,也被安葬在了家乡的“海滨墓园”。对于艺术家郭宇剑而言,这也许是个关于“在地”的巧合,他结束意大利的留学生活后,毅然而然地回到了家乡长沙创作生活。
- Dangerous Complicity, ©ARCH GALLERY 2022
- Dangerous Complicity, ©ARCH GALLERY 2022
在此次展出的新作品中,我们总能观察到成对出现的形象,或撕裂画面某处的轮廓,或恬淡地渐隐在色块中,这里似乎蕴含某种非叙事的野心:绘画必须将形象从“具象的”那里抢过来。“不是要表现可以被看见的东西,而是要让东西可以被看见。”可这谈何容易,连培根[5]都这么说:“但是,在一个形象与另一个形象之间讲述的故事从一开始就取消了绘画通过自身而起作用的可能性。这里存在着一个非常巨大的困难。”[6]德勒兹在评论培根的绘画时如此描述这个困境:“在两个形象之间,总会有一个故事滑进来或试图滑进来,以给图解表现的整体带来生机。所以,孤立是最简单的手法,是必需的,虽然并不够,其目的是与表现决裂、打破叙述、阻碍图解性的出现,从而解放形象:只坚持绘画事实。”[7]德勒兹将这种形象间“非图解性的、非叙述性、甚至非逻辑的关系的可能性”称之为“不可争辩的事实”。
- Dangerous Complicity, ©ARCH GALLERY 2022
许是因此,郭宇剑的绘画总是呈现出别样的生成律动,仿佛画面正好定格于形象即将成为“事实”的瞬间,但从另一种运动的方向上,气韵氤氲的笔墨也可以理解成一种消散,如若我们对比画家更早的作品,这种“消散”作用在许多层次,更为精炼的色彩,更为混沌的构成以及更不可定义的趣味。正如德勒兹所提到的,画家从来不是面对一个空白的画布工作,“在画布的表面上,已经潜在地存在着各种各样、必须与之决裂的零碎图像”,“画家所做的,不是要填满一个白色的空间,而是要清理它、扫除它、清除它”,优秀的画家总是在有意无意与动笔前画布上已有的俗套图像做着搏斗,与本身既有的审美情趣和熟练的技艺性做搏斗,避免对俗套图像做出智性的、过于抽象的回应,而使得媚俗从灰烬上重生。
- Dangerous Complicity, ©ARCH GALLERY 2022
- Dangerous Complicity, ©ARCH GALLERY 2022
- Dangerous Complicity, ©ARCH GALLERY 2022
几年前观看郭宇剑的画作时,我曾写道:“我凝视着画面时,有什么东西也凝视着我。”这种“被事物思考着”的奇妙审美体验,在其新的系列作品中逐渐复杂化。随机却又被沉稳操控的笔触、模糊却又无比精准的形象,将观者游移的目光紧紧裹挟,同时让他们的判断力成为了作品的一部分。像谜题般被艺术家安置在展示空间中的文字片段和符号,与其说是对画作的补充和解释,不如说是一种审美上的“扰乱”,艺术家本就无意让观众“看懂”画作,首先是感受,而非智识上的共振。
- Velvet 2, Oil on canva, 20x20cm, 2022
- Velvet 3, Oil on canva, 20x20cm, 2022
- Velvet 4, Oil on canva, 20x20cm, 2022
“危险同谋”的“危险”二字,于我的理解,首先指向艺术家的创作行为。创作是一种极端体验,是波德莱尔[8]所说的“艺术家在被击败的一瞬间发出的恐怖的叫喊”,是梵高[9]留下字条里的“我的理智已经有一半融化在里面”,是塞尚[10]的“深渊”或“灾难”。而危险的第二层意味,藏在作品“以外”。这里我们可以借用德里达[11]在《绘画中的真理》里提到的“边饰”(Parergon)概念,所谓边饰,并非作品的边缘或画框,可以理解成作品外的附属物,在展览的框架下,章节引言似的文字片段、被涂上颜色的墙所构筑的空间、投影在墙上的乐谱、甚至连作品准备阶段的小稿都可算在此范畴。对德里达而言,边饰既属于作品又不属于作品,处在某种非内非外、既内又外的边缘。郭宇剑此次的展览中,艺术家与策展人共谋的精巧细节,同时在构成和解构作品,它们既是画家的笔法和手势,也是画家刻意撕开的、危险的裂痕,这里只有非罗格斯(logos)的逻辑,理解被悬置,官能在游荡。
- Dangerous Complicity, ©ARCH GALLERY 2022
行文至此,这篇文字也成了《危险同谋》的边饰,无意也无法成为展览的解读。而关于绘画的真理,套用塞尚那句著名的述行性话语(也是德里达《绘画中的真理》标题的由来):“我欠您绘画中的真理,我会对您说的。”这“亏欠”的真理,或许终究无法被我们的语句言说,但画家将以生命为尺度,在一笔一划间缓缓地履行自己的承诺。
[1] Paul Valery,1871-1945
[2] The Graveyard by the Sea, poem by Paul Valéry, written in French as “Le Cimetière marin” and published in 1922 in the collection Charmes
[3] André Gide,1869-1951
[4] Andre Gide-Paul Valery: correspondence, 1890-1942. Self-portraits, the Gide : Valery letters, 1890-1942
[5] Francis Bacon,1909-1992
[6] Interviews with Francis Bacon, David Sylvester CBE
[7] Francis Bacon: Logique de la sensation, Paris: Editions de la difference, Gilles Deleuze, 1981
[8] Charles Baudelaire,1821-1867
[9] Vincent van Gogh,1853-1890
[10] Paul Cézanne,1839-1906
[11] Jacques Derrida,1930-2004